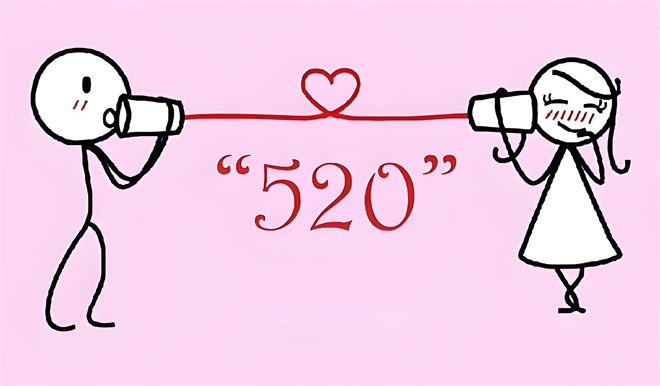
两情侣分手后,一方要求另一方支付借款费用,而其中一方却说“恋爱款项”不应返还。近日,柳北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因特殊关系引发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法官在经过耐心细致审理后,认真厘清了两人诸多经济纠纷的法律关系,依法作出判决。
女子黄某和男子廖某相识于2019年,后两人发展成为男女朋友关系,于2023年7月份左右分手。黄某称,廖某因资金周转需要先后多次向其借款83889.25元,她通过刷信用卡、微信、支付宝转账等方式分多次向廖某支付了出借款项,并对廖某催还出借款项,但廖某至今未归还,故诉至法院要求还款。廖某认为,两人曾是恋爱关系,黄某向自己转款项为情感款项,不是法律意义的民间借贷。廖某与黄某之间历经多次分手,双方均对恋爱、同居期间的生活开销产生争议,并没有针对其中任何一笔款项或者任何一个金额达成借贷合意,应当认定黄某的借贷要约并没有得到廖某的最终承诺,双方之间并不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因此廖某请求法院予以驳回。

黄某曾向廖某发送过大量催促被告偿还信用卡及网贷的信息,其中廖某承诺给黄某一笔8000元分手补偿费用,黄某提到过“那三千肯定是要还我朋友的”,廖某承诺“如果没别的意思,话题就打住了吧,8000块钱会一分不少的给回你”。

法院审理后认为,该案系因原、被告恋爱期间的经济往来引发的纠纷,男女双方在恋爱中,应树立正确的恋爱观,不得仅以物质利益换取对方感情,也不应借恋爱换取对方钱财。黄某诉请的金额由三种性质构成,一种为信用卡、网贷所产生的31739.25元,一种为微信、支付宝、银行转款及现金共计44150元,一种为双方分手时被告廖某承诺支付的8000元。
对于信用卡、网贷所产生的31739.25元,因廖某认可为“以账还账,以卡还卡”,一直使用原告黄某名下信用卡至2023年前年后的10月,并要求黄某从各金融机构或平台贷款进行过账,被告廖某作为款项的实际使用者,应当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原告黄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晓将信用卡出借给他人使用的风险及后果,且考虑到双方同居期间的日常生活开销大部分由被告承担,法院酌情认定被告廖某承担31739.25元的70%,即22217.48元,原告黄某自行承担9521.77元。

对于微信、支付宝、银行转款及现金共计44150元,原告黄某以民间借贷纠纷提起诉讼,但除部分转款记录备注有“出借”外,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实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而转款凭证上注明的“出借”仅为原告的单方意思表示,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能据此认定形成双方合意。无法排除上述款项为双方同居期间日常生活消费或原告向网贷平台借款后交付给被告的情形。且上述款项交付后,两人之间有多次账目往来,被告廖某向原告黄某的转款数额已远超原告交付给被告的数额。据此,对于原告主张被告偿还微信、支付宝、银行转款及现金共计44150元的诉请法院不予支持。
对于双方分手时被告廖某承诺支付的8000元,该8000元中,经过微信聊天记录认定,其中有3000元系原告黄某向朋友借款所产生的,廖某承诺支付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故该3000元应由廖某承担。剩余5000元系双方为结束情感,由被告廖某向原告黄某给予的补偿,属于自然之债,原告黄某对该5000元的诉请,法院不予支持。
最终,法院判决被告廖某返还原告黄某信用卡使用额度以及借款共计人民币25217.48元,驳回黄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双方没有提出上诉。
法官说法:
恋爱期间的经济往来与民间借贷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一个复杂且微妙的领域,它不仅关乎金钱交易的性质判定,还涉及情感因素与法律原则的交织。一般情况下,对于恋爱期间经济往来,若存在借条等书面凭证或还款承诺的,可以视为借款,收款一方应当予以返还。对于“520”“1314”等具有特殊含义的转账,应认定为维系双方情感或共同生活所需的款项支出,不应认定为借款,无需返还。

关于一方出借信用卡给另一方使用的问题。根据法律规定,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民间借贷行为无效。信用卡的信用额度是金融机构基于持卡人的信用而发放的,属于信贷资金,将信用卡出借给他人使用是套取信用资金转贷的行为,因此形成的民间借贷行为是无效的。在此情况下,一方所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但因出借信用卡一方也具有一定的过错,也应按照过错程度承担部分责任。
分手后口头承诺的金钱补偿行为,属于自然之债,不受强制执行力保护,对于自然之债,当事人愿意履行的,则履行有效,如果当事人不愿意履行的,债权人不能请求法院强制执行。

一段亲密关系的结束本就令人遗憾,若“好聚”不能“好散”则更会让人叹息。故而对于曾是情侣的双方,即便分手后需要“明算账”,亦当保持冷静和理性,优先选择和解或调解之类的相对温和的解决方式,保留体面的同时减少对双方情感上的伤害。若纠纷当真无法调和,亦当理性收集证据,如实陈述事实,以便法院作出公正客观的裁判。


